伊朗当代电影大师阿斯哈·法哈蒂去年斩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新片《一个英雄》,叙事策略与他以往的代表作品一脉相承:脱胎自伊朗现实语境的故事,起点虽然简单,不过随着戏剧悬念的接连出现,情节走向变得错综复杂,主人公站在道德或情感的十字路口,表现出的无所适从,也在不断加重。
他镜头下的伊朗式困境,尽管由本土的宗教传统制约民众身体与行动赋予,却在全球范围广获观众共鸣,道出当下不同种族与信仰的人们,有着相似的生存处境。而与旧作相比,《一个英雄》由于添加了社交媒体的背景,戏剧冲突更具蝴蝶效应,俯拾皆是不可控的元素,人物的困惑与无力跟着进一步超出伊朗的范畴,适用于人类社会。
日常与戏剧
伊朗在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后,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社会结构发生较大改变。艺术家的创作偏好,往往由现实环境与个人经历共同决定。面对生活中的千疮百孔,以及较为严苛的电影审查制度,自诩更像诗人而非导演的世界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长流》等佳作中,用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方式诗意呈现细微事件,让观众看到古老的波斯文明,依旧是伊朗当前社会的光明灯。同时,他借助《如沐爱河》《合法副本》等作品,将关注的人群的范围,由伊朗孩童扩大至世界各地的成年男女,揭示人类整体的生存现状。
以虚实融合的手法关照脚下的土地,同时反映人类的共同境遇,也贯穿于莫森·玛克玛尔巴夫、贾法·帕纳西等伊朗名导的创作。
与这些前辈相比,法哈蒂的多数影片也是立足伊朗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散发着真实动人的光芒,具备普世价值。不过由于法哈蒂本科与硕士念的都是戏剧专业,他喜欢采取带有一定巧合与离奇色彩的戏剧手段,而非纪录片式的“客观”视角再现日常种种,通过对伊朗传统与现代并存环境的展示,道出社会各个阶层尤其城市中产阶级的窘境。
他的电影,通常会让一个身份与片中其他人相比有些特殊的人物,以偶然介入的方式,带领观众走进一处处宛若戏剧舞台的封闭式空间,譬如家庭居所、寺庙、监狱等,让银幕之外的我们,不仅窥见从日常生活中生发的事件,如何在空间里面渐渐失控,也洞悉空间外面的社会土壤的变质情况。
《烟花星期三》里出身底层,对婚姻充满憧憬的伊朗女孩,在一户中产家庭做家政服务时,除了意识到面前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也像个观看了一出沉浸式戏剧的观众一样,见证了婚外情对于该家庭面貌的无情改造。走出看似与她无关的破碎之家,街头巷尾释放着危险信号的焰火映入眼帘,社会直观展现出飘荡不定的环境,她陷入有关自己未来婚姻走向的思考。
法哈蒂运用戏剧手段最为极致的例子,当属他2017年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推销员》。片中,以戏中戏形式贯穿的阿瑟·米勒的剧作《推销员之死》,和伊朗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一对中产夫妻尹麦德与蕾娜的情感起伏,均形成呼应。
影片伊始是工人搭建《推销员之死》演出所用舞台的画面。脚手架上闪烁不停的酒店霓虹招牌,指向怀揣着美国梦常年在外奔波的推销员威利的日常归宿。对他而言,灯红酒绿的天地比居家生活更有吸引力。但脚手架的摇摇晃晃,也在预示将来美国梦的倾塌,威利不仅会失去风尘女子在酒店为他营造的“温柔乡”,也会与家中的妻子渐行渐远。
戏里讲述昔日的美国,轰隆向前的时代列车如何将小人物无情碾压,戏外并置道出当下的伊朗,个体的生存空间同样在被无情摧毁。在这部剧中扮演威利与妻子的尹麦德与蕾娜,夜半三更睡眠正酣之时,被巨大的轰鸣声吵醒,楼下的挖掘机正在动摇他们居住的楼房的根基。他们对于挖掘机的突兀“来访”,并没表现出丝毫惊讶,说明此类事情早已屡见不鲜。中产人士基本的生命权利尚且得不到保障,底层人群的生存状况可见一斑。
随着地基的松动,两人卧室的墙壁上也出现了裂痕,道出社会与作为社会基石的家庭之间,存在唇亡齿寒的关系。两人搬到新的住处之后,正在沐浴的蕾娜听到门铃声响以为是丈夫回来毫无警惕地开门、闯入浴室的陌生男人对她施暴等戏剧性时刻的接踵而至,让他们的情感逐渐由亲密走向疏离。
《一个英雄》中虽然没有对于经典剧作的化用,剧情亦是处处可见戏剧化的笔墨。因欠债入狱的拉辛利用假释,与女友法尔孔德去金店售卖她在银行意外捡到的十几枚金币,想着也许可以偿还债权人大约一半的债务,让债权人撤销对他的起诉。当发现金币的价值低于预期,店主的签字笔又写不出字,他似乎看到了真主的启示,把金币拿到姐姐家里,于次日在银行附近张贴若干张寻找失主的告示。不久,一位自称金币拥有者的女士,从姐姐手中取走了它们。拾金不昧的他,被电视台塑造成为“一个英雄”,同时获得慈善机构的帮助,拿到一个工作机会。
然而丢失金币的女士可能并不存在的传闻,让拉辛的公众形象开始受损。他遍寻这位女士无果,为了得到工作让法尔孔德假扮失主,事情失去控制。
经书与私欲
法哈蒂以往的作品里,不乏恪守宗教传统的信徒。2011年令他名声大噪,先后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大奖的《一次别离》,女护工面对患有老年痴呆的纳德父亲的如厕失禁方寸大乱,按照《古兰经》的教义,她不能触碰丈夫以外的任何成年男性的身体,但站在人道主义以及护工职业的立场,她应该立刻帮他清洗身体。她给宗教协会打电话,被告知安拉会宽宥她的行为,方才动手把老人清洗干净。
《一个英雄》里尽管缺少经书的影踪,但是片头出现的埋葬大流士一世等四位波斯帝王的纳什洛斯陵墓,充当的却是类似《古兰经》的功用,象征着伊朗根深蒂固的传统。传统关联个人尊严、家族颜面、社会礼仪,是好是坏暂且不论,技术工人对陵墓的尽心修缮,说出时至今日,传统在伊朗人的生活里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左右着他们的行动。
拉辛姐姐便是传统的忠实守护者。她看到金币之后,让拉辛以母亲的名义发誓,“永远别做任何让你和家族蒙羞的事”。她担心这些金币是拉辛偷窃所得。
不过从结果来看,信徒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遵守,似乎并不值得。片中的债权人本分老实,与拉辛原本既是合伙人又是连襟。两人一起做生意时,他为了帮助拉辛,几乎赔上了全部家当。他把拉辛送进监狱,着实是因生活陷入泥淖。拉辛成为“一个英雄”之后,民间舆论显露不分青红皂白的面相,“逼迫”他免除拉辛所欠的大部分债务。
或许正因如此,法哈蒂刻画的大部分人物,属于传统的背离者。《一次别离》中护工的丈夫为了从纳德手里拿到一笔数额不菲的赔偿金,不仅把手放在《古兰经》上撒谎,还要妻子一起违背经书的旨意。《一个英雄》里的绝大多数人,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隶属行政机构、公益组织、服务行业的员工的行为,距离经书教人诚实、守信、向善的基本教义也都相距甚远。
对于拉辛归还金币的举动,法尔孔德颇为恼火,银行的工作人员则悉数流露“这家伙有病”的迷惑表情。拿走金币的女士是位假冒者,她用伪装骗取了拉辛及其姐姐的信任。拉辛能够成为“一个英雄”,是监狱负责人化解囚犯自杀风波的结果。为拉辛募捐资金的慈善机构,也把他当作宣传公益形象的工具,利用他患有语言障碍的儿子,博取公众的同情。网民在拉辛对债权人大打出手的视频里,发现他与“金币失主”原是情侣,开始就看到的所谓真相对他展开舆论谴责,并没去想带着拍摄者主观立场的影像具有片面性。
拉辛本人亦是如此。他决意将金币物归原主,不是因为真的看到了真主正在考验其灵魂,而是姐姐的言语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刺激。他在告示上留下监狱的电话而非姐姐或自己的手机号,更是怀着目的。他预想了这件“好事”,会带给他的世俗荣誉与切身好处。
探究这些人物的言行打破教义的原因,除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更为关键的也许是,某些传统理念对人性构成了无形的压迫。《一个英雄》开场的远景镜头,巍峨的陵墓与渺小的拉辛形成的鲜明视觉对比,说明了一切。
但反抗传统并不意味着放弃信仰。法哈蒂与阿巴斯一样,认为活着的人需要信仰。而提供信仰的源泉,不是带有虚无色彩的真主或者天父,而是自己的本心。
片中见证拉辛被冒领金币的女士欺骗经过的出租车司机,为了让这位年轻人能有活路,心甘情愿帮他作了伪证。影片临近尾声,无路可走的拉辛在监狱工作人员的建议下,答应再度利用儿子的眼泪,以便换取看客们的原谅与同情,挽回个人与家族的社会声誉,但意识到“表演”会给儿子带来终生的心理创伤,他击碎了听起来完美的计划。
拉辛最初为了能够出狱,让自己成为精于策划的布局者,最后却主动做了出局者,心平气和地走进监狱继续服刑,不再在乎公众的情绪会否发生逆转,事情的真相会否被永远遮蔽。正是因为内心有了真正的信仰,他走出了法哈蒂电影中常见的困局。
社会与女性
《一个英雄》与法哈蒂以往作品形成关照的,还有他对于伊朗女性命运的追问以及两性相处模式的反思。
女性运动已在全球范围取得显著成效,不过在伊朗等国家任重而道远。法哈蒂的影片里,女性的着装虽然不像律法规定的那般严格,她们地位卑微难有话语权,却是不争的事实。男权社会的语境里,包括丈夫、父亲、兄长、朋友等在内的伊朗男性,站在宗教与道德的高地,因为考虑个人或家庭的颜面无视女性的尊严,把她们推到尴尬难堪甚至无法承受的境地,是法哈蒂电影中常见的主题之一。
《推销员》中的尹麦德在妻子遭到陌生男人的暴力侵袭后,表面上对她关心备至,但因为忌讳她的身体被施暴者与救助她的男邻居看到,有意与她保持着身体的距离。尽管蕾娜一再哀求他忘记此事,他仍然对施暴者究竟是谁展开秘密调查,并在过程中一次次撕开妻子渐渐痊愈的心理伤口。《美丽城》中一心为死于非命的女儿复仇的父亲,在已故的女儿眼里,也许是个合格的家长,可是他对于腿有残疾需要及时医治的继女、照顾他饮食起居的现妻,态度非常冷漠。
《一个英雄》里法尔孔德的哥哥,原本因为拉辛有服刑、离异、膝下有子等问题,竭力反对妹妹与他在一起,认为这会严重损害家族尊严。在报纸上看到拉辛的英雄事迹,他同意了两人交往。得知拉辛的事情出现大反转,他又对妹妹大发雷霆。这一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把法尔孔德的感受当一回事,完全不在乎她把拉辛视为唯一的真爱,介意的始终是社会的评价眼光。
伊朗女性面对以婚姻为代表的社会藩篱,除了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还能做些什么?法哈蒂给出的答案是,哪怕要付出沉重代价,也要主动尝试冲破。《关于伊丽》里待嫁的伊丽,以神秘消失的方式,逃离了未来婚姻可能带给她的压迫。《美丽城》《烟花星期三》《一次别离》里的已婚女性都选择了离婚,其中《一次别离》里西敏离婚的目的,不单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能够离开伊朗,让女儿拥有崭新的成长环境。
不过正如法哈蒂尽管质疑宗教,却相信信仰的力量,他并没有因此全盘否定婚姻与家庭。《烟花星期三》里雇主的婚姻闹剧虽令女孩忧心自己的未来,但男友深夜站在街头吹着冷风接她回家的行为,让她绽放笑容,对两人的婚姻重拾信心。《美丽城》里对丈夫绝望的女人,从闯入她生命里的陌生男孩身上,看到了异性美好的品质。
显然,在法哈蒂看来,女性运动不能只靠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自身的行动,男性的挺身而出也很重要。国家意识、宗教律法、传统习俗等共同决定的社会氛围的改变,虽然需要群体合力才能一步步完成,但在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的内部,男性至少可以收起大男子主义,给予女性应有的尊重。家庭内部的两性关系得到改观,社会才有改良的希望。
回到《一个英雄》。拉辛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法尔孔德都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她与拉辛的儿子一起送他返回监狱的画面,侧写出她要与两人组建三口之家的决心,令观众既心酸又感动。结尾拉辛坐在暗处等待办理入狱手续时,看到出狱的老人与接他的妻子在阳光下开心团聚,则让观众预见了他与法尔孔德的未来。
这些笔触,包含法哈蒂对于坚守内心信仰的普通人的致敬,以及他对于两性关系乃至社会前景的期许。同时,它们流露出法哈蒂作为艺术家,对于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的善意与柔情,就像他的电影虽然随处可见戏剧性,但对于那些刺激眼球的戏剧化场面,比如《推销员》里蕾娜被暴力侵袭的过程、《一个英雄》里拉辛如何被网络施暴等,并没直接展现,而是予以留白处理。(梅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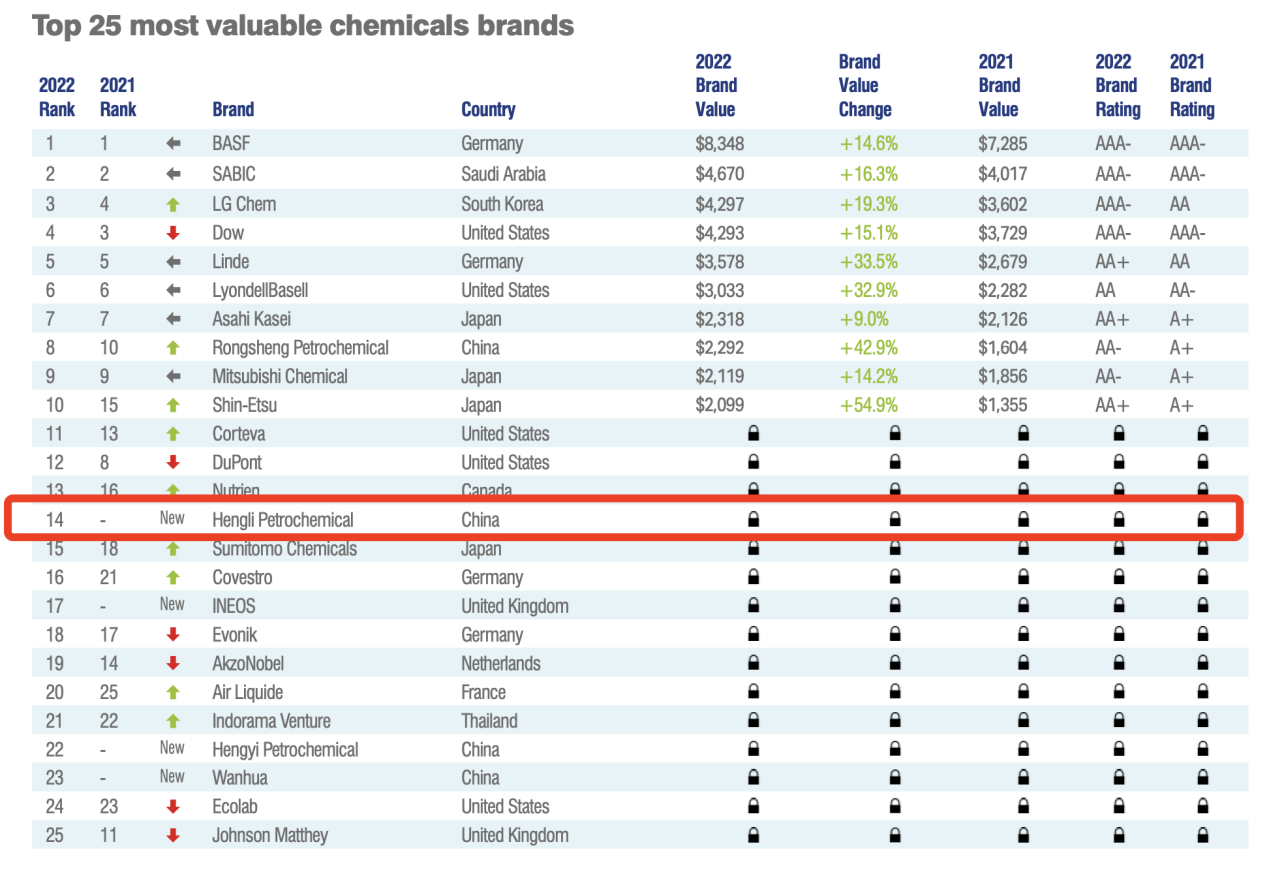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