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鲜”的俄罗斯戏剧将登上中国舞台
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世界著名的戏剧大国,中国观众通过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阿尔布卓夫、罗佐夫和万比洛夫等作家和戏剧艺术家的作品,了解了俄罗斯19世纪和20世纪的戏剧经典。而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戏剧都有哪些变化和新面孔呢?被世界各国和本土剧目所充盈的中国戏剧海报上,难得见到俄罗斯剧目,尤其是当代剧目了。值2018年中俄文化交流年之际,得益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的合作,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共同组织了《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五卷本的《俄罗斯当代戏剧集》应运而生,收入的剧作达23部之多,可谓我国近年引进的俄罗斯剧作之最。即将于下月在中国舞台上呈现的两幕喜剧《高级病房》,正是出自这部戏剧集。
受贿和偷情的双重败露
《高级病房》的作者亚历山大·科洛夫金既是作家,也是演员和戏剧活动家。他毕业于俄罗斯最负盛名的国立卢那察尔斯基戏剧学院表演系,后在高尔基文学院戏剧系学习,毕业后进入莫斯科著名的高尔基艺术模范剧院做演员,参演过我国观众所熟悉的俄罗斯导演费多尔·邦达尔丘克、伊·德霍维奇内和阿·西连科的电影作品。除了做演员,科洛夫金还是个活跃的剧作家,创作有《新娘的木偶》《关于爱情》《麻子脸的鬈发》《男人和卷心菜》《高级病房》《有水果的房间》《怪物》等剧作,并且也是俄罗斯知名的影视剧编剧,有轻喜剧《编辑部》、犯罪题材电视剧《土耳其进行曲》,以及曾风靡中国的俄罗斯宫廷剧《可怜的娜丝佳》(我国翻译为《情迷彼得堡》)等作品。曾经在俄罗斯《当代戏剧》杂志担任主管的工作经历,则为他探索戏剧体裁提供了很好的视野与平台,以使他对俄罗斯当代喜剧和“闹剧”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在人们的印象中,正剧和悲剧似乎可以更好地呈现出戏剧的样貌,有庄严的仪式感,充满着高尚的情操、雄浑的气概和令人敬畏的崇高之感。而喜剧则不同,貌似“神圣”的事物都会受到讽刺嘲笑。在当代俄罗斯剧坛,喜剧的创作现况因其复杂性、矛盾性和多意性,很难对其进行系统和严格分类,仅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种基本的样态,即讽刺剧和幽默剧。这两种样态在当代俄罗斯剧坛上此消彼长,我们除了可以看到通俗喜剧、怪诞剧和抒情喜剧外,也可以看到讽刺剧与幽默剧或闹剧的渐渐相融。
《高级病房》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性剧作。满心希望住进单人病房的官僚拉兹尼茨基不得已与退休的功勋演员伊祖姆鲁多夫同住在了一间被称为“高级病房”的双人病房,他们一个做痔疮手术,另一个做疝气手术。
拉兹尼茨基是莫斯科某机关土地规划司的领导,收了“巨人建筑”公司的大笔贿赂,入院之际得知事情败露时,妻子罗拉和情人让娜又先后进到病房探望,他一面安排助理即情人的丈夫处理钱款以避免受贿败露,一面害怕妻子和情人碰面造成不堪,双重焦虑和面对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的事态变化,他忽而趾高气昂,忽而焦躁不安像无头的苍蝇,以致被妻子讽刺“不是割了痔疮而是被割了脑袋”。
功勋演员一开始被官僚嫌弃,所以报复性地偷喝官僚带进病房的天价法国酒,号称对压榨普通人的“土豪”要“尽可能反击”和“维护社会平衡”,可他天性善良,虽然也知道“不能啥人都交”,不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还是有意无意地帮官僚解围。官僚助理菲利克斯原本是老实本分的人,因为金钱与利益被官僚牵着鼻子走,不过软弱的他在维护自己的爱情时依然也会振臂一呼要勒死那个让他戴绿帽子的人。
如果说官僚身上集中了剧作家对社会和现实肮脏阴暗的讽刺和批判锋芒,那么在助理菲利克斯身上则体现了剧作家对人性中诸如懦弱、愚钝和盲从等弱点的嘲讽,在功勋艺术家身上则是对他幽默品质的幽默。在这三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讽刺喜剧、幽默喜剧和闹剧的融合。
与三个身份和性格分明的男人相比,三个女人以各自情感的悲喜突显了现实与生活中的矛盾与无奈。官僚太太罗拉在物质上依赖丈夫,同时又希望与丈夫在人格上平等,她有官太太的虚张声势和浮夸做派,又有丧失独立人格的软弱心虚。在发现丈夫的私情时她的内心是矛盾纠结的,戳穿他会让自己没有退路,忍气吞声又不甘心,所以她在半信半疑和情愿与不情愿之间游移,同时也在功勋艺术家对她的爱慕恭维中找到了自信。
护士伊龙娜可以说是这出喜剧中唯一被剧作家以温和赞许的目光欣赏的人,她敬业善良又幽默风趣。她打两份工养活家人,本来想托官僚的关系给丈夫找份差事,在得知官僚的人品底细以后又自觉放弃,无奈中重回辛苦奔波的生活。在这个社会底层小人物身上,剧作家让观众看到了人所应有的人格尊严、独立自强和乐观善良。正是这样的小人物,才是社会最坚固的基石。在她的身上,我们甚至能找到万比洛夫笔下瓦莲京娜的影子。
而让娜是剧作家笔下唯一的漫画式人物,她集中了当代消费社会物质化人格的种种特征:浅薄、拜金、虚荣、贪图享乐、无情无义,甚至有些无耻。她像寄生虫一样依附于官僚,对社会和他人毫无贡献。剧作家让她最后表示出回到丈夫菲利克斯身边的意愿,这既是出于她的良心发现,也是生活的无奈。在这三个女性角色的塑造上,我们看到剧作家是如何将抒情喜剧、幽默喜剧,甚至正剧的元素糅合在一起的。
探索打破界限继承批判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高级病房》这种喜剧体裁上的互相融合和打破原有界限,在当代俄罗斯剧坛上并不少见。这种现象早在20世纪末便较为普遍,其产生缘于剧作家们力求挣脱原有戏剧的体裁范式,根据剧本内容的动态发展对传统体裁结构进行变形的总体趋势与诉求,剧作家如尤·埃德里斯、阿·斯拉波夫斯基、谢·诺索夫、叶·伊萨耶娃、列·佐林、柳·拉祖莫夫斯卡娅、斯·舒利亚科等都进行过这类尝试。
当然,世纪之交喜剧体裁边界的模糊与消融并不意味着喜剧的消失。在《高级病房》中,我们看到讽刺与幽默均保留了在体裁上的主要属性,既表现了幽默在体裁形式上更大的可能性,也让讽刺赋予了喜剧自身更强烈的特殊性,不仅提出了与时代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同时彰显出喜剧美学的新特性。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高级病房》继承了俄罗斯戏剧史上的果戈理喜剧传统,偏重了批判精神,更多属于讽刺戏剧的范畴。
除了对官僚拉兹尼茨基颐指气使、高高在上和气急败坏、厚颜无耻的讽刺,贯穿全剧始终的电视报道则更加直白和直接地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的批判态度:从莫斯科州检察官被暂停职务、警察局和检察院涉嫌参与组建非法赌博机构并为之提供庇护,到法官助理长期伪造法庭决议、莫斯科东北区官员多年来敲诈勒索、诈骗团伙伪装成社工讹诈退休老人、大型建设集团“巨人建筑”被查抄和部分官员收取高额回扣,等等。可以说,透过这种种现象,苏联解体以后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社会乱象几乎被一网打尽,难怪护士伊龙娜会说:“以前就知道中饱私囊,现在简直毫无变化!”而主播的声音在剧尾再次响起:此前媒体关于“巨人建筑”总部被搜走大量文件的消息是谣言,公司运转正常,检察院方面对其并无非议。看来,官僚拉兹尼茨基的处境又化险为夷了,其妻子罗拉并没有因为让娜而与他彻底决裂。
与传统喜剧有所不同的是,《高级病房》并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也没有像《钦差大臣》以“哑剧”收场,让“恐惧心态”继续蔓延,这种恐惧产生于负罪的良心,同时也是对良心负罪者的惩罚。我们可以看到,剧作结尾完全脱离了喜剧的轨道,向正剧偏离和靠近。这样的结构和设置,强化了剧作家对社会与生活的态度,体现出他对喜剧边界的一次大胆探索。
果戈理和契诃夫的后人怎么做
与时代相伴改变的,还有喜剧中笑的特性与它的表达形式。《高级病房》中的笑,有的来自于人物性格的缺憾,有的来自于对话所碰撞出的机巧,而大多则来自于空间和时间叠加以后所产生的紧张效果。在病房这个局促的空间,六个人物分别进进出出,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巧合、错过、逃离尴尬的动机与避免相遇的说谎。
在剧作家大显身手的种种巧合中,全剧的冲突被聚焦了,那就是受贿和情人的双重暴露。这是双重的焦虑,也是双重的恐惧。在焦虑和恐惧的作用下,巧合就成了环境所提供的机遇,让剧作家主要嘲讽的对象官僚拉兹尼茨基的真实面目得以暴露无遗。
与传统喜剧给出规范的处方和道德说教般建议不同,当代喜剧在笑声中所揭示的是与人物本质紧密相连的生活。对拉兹尼茨基的笑,是痛快淋漓和愉快的笑,这种笑是对他的救赎和对我们自身的净化;对菲利克斯的笑虽然是愉快的,却伴随着苦涩的讽刺,因为这笑与苦涩的讽刺背后,是对他懦弱和盲从本性的同情与批判。但《高级病房》中所运用的制造笑的重要方式却并不陌生,可以说与传统喜剧还一脉相承,即利用隐瞒和说谎来主导情节的推进。早有19世纪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当代有戈林的《稀奇的事》、布拉津斯基的《二人游戏》和科利亚达的《波斯丁香》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当然这也是讽刺喜剧常用的手法。
如何使剧情推动、笑点迭出呢,科洛夫金在采访中作了这样的自述:“很久以前我就在竭力寻找某种风格,但不久前才找到。它叫情境喜剧,准确来说,是‘卧室喜剧’。在俄罗斯没有一个剧作家按这种风格创作。最早探索这种风格的是法国剧作家尤金·斯克里布……斯克里布把这种风格称作‘编号法’。创作时,他和助手一起改造情节,把故事揉匀。当某种东西打动斯克里布时,他就在编号下方写上‘精彩之处’,然后按照编号来构筑剧本。重点在于,情节要动态发展,复杂的纠葛要维持不变……要在第一时间就发生复杂的纠葛,随后这个纠葛会以意想不到的转折、冲突的方式出现,想要摆脱它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科洛夫金的这种情境创作法在《高级病房》中的确可以寻到踪迹,虽然在表述上像一个呆板的流程,但作为具体可行的方法却可以将作家、剧作和观众这三个戏剧创作的节点联系贯穿起来,共同服务于他所要表达的人生态度、社会立场和戏剧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洛夫金的确是非常注重剧场效果和观众反应的剧作家,他在喜剧领域的探索的确是全方位的。这一点,也符合当今世界戏剧观念发展的潮流。
《高级病房》创作于2011年,2014年搬上戏剧舞台。除中心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北起摩尔曼斯克,东至海参崴和哈巴罗夫斯克,中部有伏尔加格勒等地,这出戏走遍了俄罗斯境内一百多家剧院。截至今年上半年,仍有不少剧院将其列入排演计划。时过十年,这出戏即将呈现在中国的戏剧舞台。
应该说,这是登上中国舞台的最“新鲜”的俄罗斯戏剧作品。面对与我们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品,中国的青年导演徐小朋和演员们会怎样去诠释?中俄观众的“笑点”一致吗?而近十数年习惯于沉浸在契诃夫戏剧中的中国观众,该如何接受果戈理和契诃夫的后人们关于喜剧的探索呢?这些探索又能为中国的喜剧艺术带来怎样的启示和思考呢?中国的观众与远在俄罗斯的科洛夫金一样,都对这次中国艺术家所上演的《高级病房》充满了期待。(苏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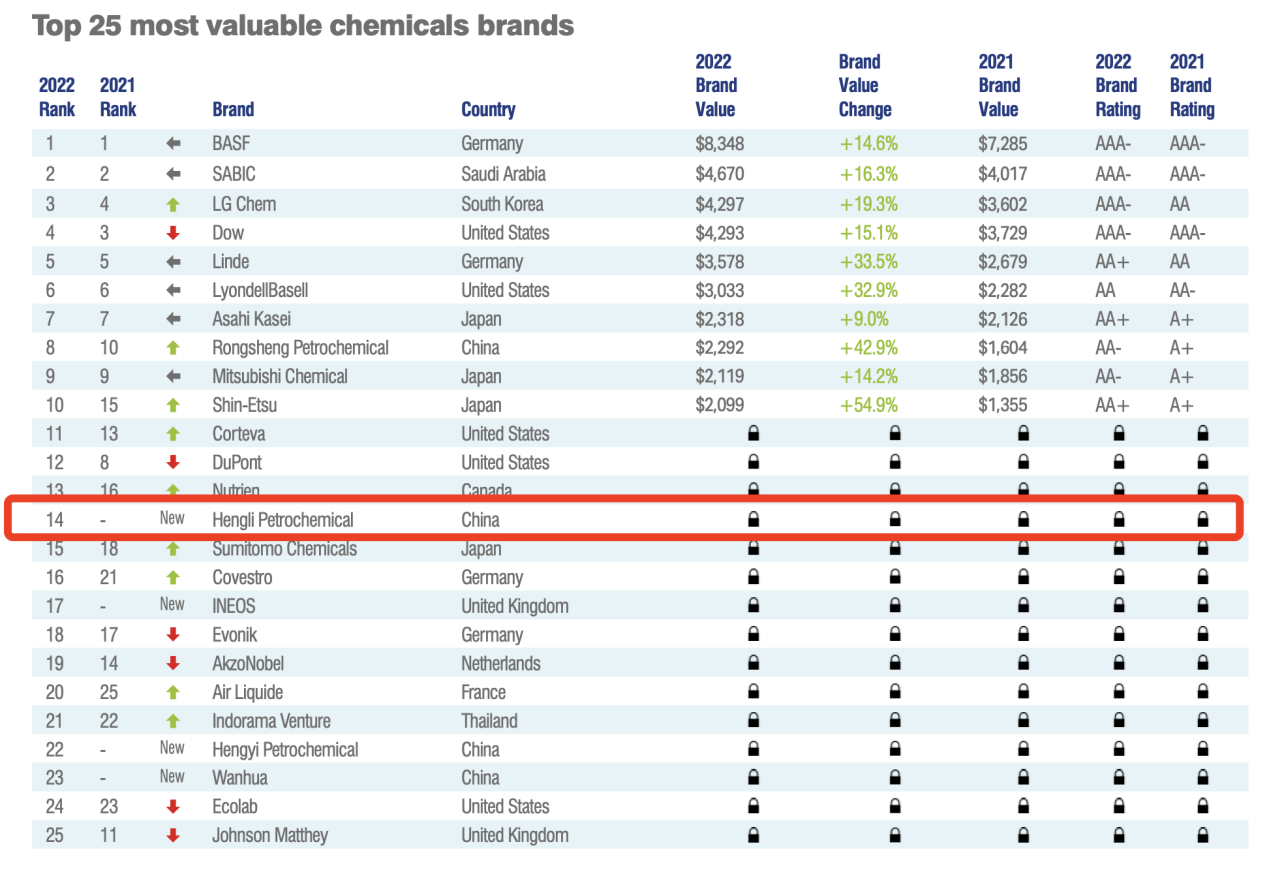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